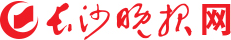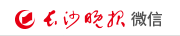米粉里的常德味
■林成燕
晨起一場暴雨,,澆滅了前幾日驕陽的氣焰,。暴雨不常有,而賣粉的小販在我們常德城內(nèi)卻常常來到身邊,。賣米粉的小販照例在早上七點準時出現(xiàn)在我們小區(qū)門口,,一聲又一聲悠長響亮的“挑(tiǎo)粉嘍”“擴”入我的耳朵里。美夢的痕跡已褪去,,混沌的大腦預備重啟,。奶奶拿著裝粉的小篩子,買上3元的粉,,走入廚房開始忙碌,,燒開水、備涼水,,準備下粉,。
白圓滑潤的米粉像長長的細線,串起了我在今年夏天的早晨,,因在異地求學無法品嘗到的正宗常德米粉的遺憾全都彌補回來了,。那小販的吆喝也化成愉悅的音符,在庸常的日子里跳躍著,。我愛吃粉,,勝過吃面。家里吃粉比餐館里吃粉要簡單得多,,沒有澆頭,,放點油鹽醬醋,再加點剁辣椒,,香味也是緊緊勾人胃口的,。
米粉在今天的常德,已然成為這座小城的食文化符號,。比起其他城市響當當?shù)娜藲饷朗?,常德米粉顯然低調(diào)得多。但愛它的常德人,,哪怕在異鄉(xiāng)聽到一句“嗍粉”,,也會覺得無比親切;習慣它的人,,早已讓它的味道默默沁潤五臟六腑,,它是離家前的最后一碗鄉(xiāng)愁,也是回鄉(xiāng)后的第一碗喜悅,。
在常德,,最好吃的粉店從來沒有定論。它可以是大名鼎鼎的“劉聾子米粉”,也可以是汽車站,、火車站,、市中心的街邊小店,還可以是無意間就望見的“米粉,、包子,、饅頭供應”。
隨意走進一家米粉店,,可以看到門口的一側(cè)擺放著大鍋,,里面裝著隨時能沸騰的大鍋熱水,另一鍋里裝著澆頭,,紅燒牛肉,、青椒肉絲、三鮮……價格從7元到11元不等,,漏斗狀的木篩子盛著一定分量的米粉在沸騰的熱水里發(fā)揮它的功用,,高傲地顯示它作為下粉工具所具有的無可替代性。古舊的長凳有序地擺在幾張桌子面前,,只有斑駁的它,,才能顯出小店的正宗。若坐下去不留神,,那被翹得老高又急促落地撞得“砰”的一聲響的另一端往往會帶來尷尬,笑笑作無可奈何狀,,容易從其他食客注視的目光中解脫出來,。方桌子上常擺放著剁辣椒、酸豆角,、腌咸菜,、辣蘿卜干,它們幾乎是每家粉店的標配,,在粉里加上這些干菜,,是美味中的美味。
小店老板是隨性又自在的,。他們或是和鄰家扯著閑談,,或是在不緊不慢地洗著什么,或者是在愜意地刷著手機,,有人來了就招呼,,沒人來自得清閑。我有次去一條小街上吃粉,,店老板正坐在板凳上哼著歌,,見客人來了,不慌不忙地從板凳上站起,起來的時候還不忘扶一下板凳,,一邊走進下粉的小隔間一邊從容地問我,,“吃么得?”“一碗紅燒牛肉粉,?!蔽彝鴿差^,偷偷咽了下口水,?!?塊。微信,、現(xiàn)金都要得,。”他交代完,,就忙著下粉去了,。“老板,,看一下,。”我把微信支付的界面拿給他看,。他沒看我,,繼續(xù)下粉,“沒得事,,給了就要得,。”等我吃完離開時,,他又坐在那條長板凳上,,繼續(xù)哼著歌。
常德這座城,,有狂歡,,有笙歌,有大手一揮的豪闊,,但更多的,,是日日上演著的普通人的浮世悲歡。一家米粉店,,總是在白天黑夜里證明著它存在的意義,。
也許是一群離家打拼的人聚在一起吃碗粉就要去趕開往遠方的火車;也許是一個從遠方歸來的人才下火車就迫不及待吃碗粉嘗嘗家的味道,;也許是既不趕路又非遠歸的人剛好餓了,、渴了、累了走進店里歇歇腳,,吃碗米粉填填肚子,;也許是身上的錢所剩無幾的人吃完一碗粉就要去吃不計時日的泡面。米粉店里的人從來不體驗生活,,他們只是填飽肚子,,認真活著。
無論是在城里還是在農(nóng)村,,米粉味都已經(jīng)滲入了這座城的肌理,。正如我爸每次北上打工,出發(fā)的那天早上奶奶總是為他做好一碗香噴噴的肉絲澆頭米粉,,有寄托也有不舍,。而我,總是當別人問起常德有什么美食時,,我都毫不猶豫地回答:“米粉,!”
每座城市的煙火,相似的是它的現(xiàn)代化,,而獨特的,,則是它的文化。
>>我要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