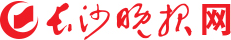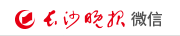影評 | 費里尼 記憶的光影捕手
■谷時段
費里尼的電影有一種潮濕感,伴著海風,,在夜色薄霧中,,交匯夢境與現(xiàn)實。怪誕,、超驗的風格,讓人不禁想起卡夫卡或是布努埃爾的作品,,而小丑馬戲團就像喚起回憶的瑪?shù)氯R娜蛋糕,,將人們帶入導演幽邃的記憶隧道。
1920年,,費里尼出生在意大利北部海港城市里米尼,,在濃厚的宗教氛圍中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十八歲離開家鄉(xiāng)來到羅馬,。在日后的電影中,,這段法西斯陰影下的童年時光,,被填充了一絲夢幻的氣息,過往的煙云給真實罩上了朦朧的色彩,。童年生活成為破譯費里尼混合著幻想和巴洛克風格影像迷宮的密碼,,但這并不意味著影像是對回憶的如實反映,作為費里尼想象物的根基,,“虛構的自傳”反映了其潛意識愿望,、理想和本能。
談到費里尼,,自然也繞不開他與同時代意大利電影的聯(lián)系,。戰(zhàn)后意大利百廢待興,電影人也早已厭倦法西斯時期,,浮夸的白色電話片,,“街道”和“斗爭”成為新口號,把攝影機扛上街頭,,運用自然場景,,啟用非職業(yè)演員,揭露真實的現(xiàn)實狀況,,講述平常人的故事,。費里尼卷入了這場偉大的電影運動中,參與了羅西尼里等人的電影創(chuàng)作,。樸素,、粗糲的影像制作,自然滿足不了創(chuàng)作者與觀眾的熱情,,羅西尼里開始在空間坐標上與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決裂,,例如《戰(zhàn)火》中沼澤和森林的場景,這樣一種在習以為常中捕捉和界定事實,,看到事物的里里外外,,揭示其玄妙、生命力的觀念深深影響了費里尼,,其影像表達也從窮街陋巷轉(zhuǎn)型到精神世界,,這些來自電影作者的能量,無限拓寬了意大利新現(xiàn)實主義的道路,。
縱觀其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明顯的變化弧線:從受新現(xiàn)實主義影響,主題上表現(xiàn)戰(zhàn)后意大利年輕人成長的《浪蕩兒》(意大利俚語,,指自吹自擂的年輕人,,字面可譯作“生長過快的小牛”),,到大師的初探《大路》,、《卡比利亞之夜》,,再到以《甜蜜的生活》、《八部半》為代表的極度風格化創(chuàng)作巔峰,,以及接下來隨心所欲地自我表達的《阿瑪珂德》等,。雖然影像表達上可能更玄奧抽象,有時甚至幾近于超現(xiàn)實,,但將現(xiàn)實轉(zhuǎn)換為另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影像卻是一以貫之的手法,。在費里尼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個人導演作品《白酋長》,一部有著好萊塢痕跡的意大利式喜劇,,迷戀“白酋長”的追星少女與捍衛(wèi)家族榮譽而神經(jīng)衰弱的丈夫,,所經(jīng)歷哭笑不得的蜜月之旅故事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標志性的導演風格元素:當妻子不知所蹤,男主角孤獨地漫游在黑夜中的羅馬街頭,,以及“白酋長”這一虛構形象,,對電影夢本身地展現(xiàn),還有沉默的海灘和翻滾的海浪,。費里尼嘗試通過虛實相生的手法,,講述一個接地氣的諷刺喜劇,就像他自己所說:“希望表達三個層次,,我們頭腦里所存在的:過去現(xiàn)在和幻想——夢幻境界,。”
費里尼并不是一位忠實的記錄者,,但他真誠地捕捉著記憶的形狀,,在真實與夢幻中構建一個“鏡像之城”。其中,,水帶來平靜,,兩性戰(zhàn)爭停歇,懷著無法描摹,、神秘的情感,,主人公孤獨地漫游在心靈的廢墟上,吟唱著古老歌謠,。在這詩意的時刻里,,不小心闖入的人們,一道旋轉(zhuǎn)沉迷,,最終用淚水洗刷苦難,,還原人的生命中無序卻又無比純凈美好的自然本質(zhì)。
>>我要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