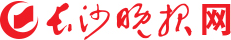何立偉:沒有了親人的老家,,現(xiàn)在是什么樣子呢,?

↑“三湘第一渡”——位于長沙縣春華鎮(zhèn)的春華渡槽
李四格子,、興姑媽,、保吾伯……我的老家的親人們
文丨何立偉
我兒時家里來的客人中,有一位叫李四格子的,,我印象至為深刻,。他一看就是從鄉(xiāng)下來的,在一堆城里人中,,顯得特別拘束,,坐是特別選到角隅里坐著,牢牢望定自己一雙腳,,好像要管住,,生怕它們亂走;又手袖著,弓起腰,,你不跟他說話,,他是一言不發(fā)的。天稍冷,,頭頂上必定戴個絨線尖頂帽,,像那種馬戲團里小丑戴的,看上去就想笑,。我父親走攏去遞煙給他,,他必躬身而起,雙手接過,,拳成作揖的姿勢,,說,還要抽你郎家的紙煙哦,。慢慢坐下,,揭開總是系著的圍裙,從里頭口袋里摸出火柴來,,點上,,拇指同食指拈著煙,掌窩著,深深吸一口,。他平常,,是自己滾喇叭筒煙抽,那煙是四個指頭捉住的,,極嗆人,,是自己種的旱煙。
我問父親何解叫他李四格子,。父親解釋說,,四,就是排行老四,,格子呢,,鄉(xiāng)下人把念過書講文明的人,或者受尊敬的人,,稱為有“格”,。李四格子的“格子”呢就是說他是一個有格的人。大概是這個意思吧,。我聽得云里霧里,,究竟不懂如何從他身上看出父親說的那種“格”來。
但有一點我是曉得的,,就是李四格子說話,,有些文縐縐,動不動就是之乎者也,。父親說李四格子是念過私塾的,,比起其他鄉(xiāng)下來的親戚,他算是肚子里頭有墨水的,。他是我父親娘家的表哥,,進城來,必定要到我家里來走走,,吃餐飯,,然后說一堆客氣話告辭而去,脅下總是夾一把暗紅色的油紙傘,。
我小的時候愛涂鴉,,拿粉筆在家里墻上四處亂畫些穿盔甲騎白馬舞刀戟的人,為此沒少挨過父親的丁公,,額角上并后腦殼上于是經(jīng)常有些轟轟烈烈的造山運動,。但李四格子是第一個表揚我的人。他歪著戴絨線尖頂帽的腦殼看我畫天兵天將,,咳句嗽,,不大不小的聲音道:咯伢子,將來有出息!父親聽見了,頗不屑,,說:亂搞,,搞得一屋邋遢得要死,有么子鬼出息,。李四格子轉過身,,對我父親說,哎,,你有所不知,,人看從小,馬看蹄爪,。你看你家少爺,,隨便幾筆就畫個神仙,幾多靈泛,。不能小看哦,不能小看,。然后就背了句我沒聽得清的古詩,,以證明他的看法是大有來頭的。父親對他的這位念過私塾的表哥是很尊敬的,,于是不爭,,悻悻道:隨他去。我雖然不大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但懵懂間還是感覺得到,,額角上的造山運動今后勢必會要少去許多。
李四格子吃飯的時候腰坐得筆直,,夾菜時筷子從不在碗里翻動,,夾少少許,放到飯尖上,,先扒飯,,再吃菜。飯要扒到碗里粒米不剩,,再去添,。我沒吃相,筷子常在菜碗里攪,,為的是尋肉吃,。亦沒少挨父親的筷腦殼——就是一筷子撲到我的后腦殼上。吃飯呢,,我父親形容我是天上一半,,地上一半——就是我吃飯,總是要掉一身的飯粒。李四格子看見了,,就扭頭對我說,,我教你一句唐詩: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然后就解釋大意,。很耐煩的樣子。父親等他說完了,,就朝我訓道:還不一粒一粒揀起來,,送到口里去。曉得農(nóng)民辛苦了啵?
李四格子瘦,,而且高,,總是彎著腰走路,仿佛世界上到處都是矮屋檐,。我長大后才明白人要有“格”,,無格不足以立世。一想到“格”,,會想到李四格子,,他走路的樣子,坐的樣子,,說話文縐縐的樣子,,還有他脅下總是夾著的油紙傘。
當然我家里客人中,,家鄉(xiāng)來的最多的是我的興姑媽,。我父親的兄姐,后來都在城里,,唯獨這位興姑媽,,仍是在北山鄉(xiāng)下。姑爹在人汽公司開公交車,,她在家里養(yǎng)豬繡花,,帶著兩個崽。進城看姑爹,,順便就來看我父親這位老弟,。不管春夏秋冬,興姑媽總是戴一頂男人戴的有檐子的呢子帽,,齊耳的黑白相雜的頭發(fā)蓬勃在帽子下頭,,使她看上去特別精神。她說話的聲氣也大,,又總是咳嗽,,我放學回來,,隔家門幾丈遠,都聽得見她說話的聲音同咳嗽的聲音,。就曉得,,我興姑媽進城來了。
并且興姑媽抽水煙筒,,手里拈一根紙媒,,呼地吹燃就來點火,然后抽得水煙筒嗬羅嗬羅響,。我每有好奇,,要拿過那黃銅的水煙筒玩,興姑媽就說,,玩不得咧崽哎,。又摸我的腦殼,問,,成績好不好來?我說好咧好咧,。伸手又要去拿水煙筒,她拍我手一下:玩不得咧崽哎,。把身體轉到一邊,。
興姑媽一來,我家里就熱鬧,,因為她愛說笑,經(jīng)常笑出一陣猛烈的咳嗽,??韧炅擞终f,還沒說完又咳,。她何解總是咳嗽呢?
我那當公交司機的姑爹倒不怎么愛說話,,瘦精精地坐著,他抽的是黃金葉的紙煙,。我小時積煙盒玩,,每央著他把黃金葉的煙盒給我。有時那盒煙根本就沒抽完,,他就把剩下的幾根倒出來,,放進上衣的口袋里,然后一聲:給!把煙盒遞給我,。我母親說,,不像話!然后跟姑爹說,你也是,,跟他認真!姑爹笑笑跟我說,,下回給你大前門的煙盒子好不好,。
姑爹也咳嗽,他有肺結核,,并且嚴重,。興姑媽咳嗽,卻只是長期的支氣管炎,。
姑爹雖精瘦,,但從小習武,有回呷了點酒,,來了興致,,就叫眾人把飯桌移開,在屋子里打了一路拳,,干凈利落,,虎虎生風。興姑媽在旁邊抽著水煙筒說,,兩三個男子漢,,攏不得他的邊。我叫著說我要跟姑爹學打拳,。興姑媽摸我的腦殼,,說崽哎,你還是念書有出息,。姑爹說,,教他兩手防防身也好。興姑媽眼睛一瞪,,說,,教么子教,教了好叫他跟別人打架是啵?姑爹就不作聲了,,表示他是懼內的,。當然,這只是當著眾人的面,。也當然,,姑爹心疼姑媽,他發(fā)了工資,,悉數(shù)交姑媽,。于是興姑媽說,這叫粒米駕揚州——就是說一切權利歸蘇維埃,。
但老家來的客人中,,我最喜歡的還是保吾伯。他是父親的表哥,。不過他不是從鄉(xiāng)下來,,是從城里來,,因為他在一家做半導體收音機的工廠里當工會干部。赤面濃眉,,笑聲爽朗,。一來,就從口袋里掏幾粒糖粒子給我吃,,每回都是太妃奶糖,。我母親說,慣飼,。保吾伯就爽朗地笑,。而且他來還是騎單車來,是一輛飛鴿牌的,。我就叫他教我踩單車,。我人小,坐到座凳上夠不著蹬子,,就左腳站在腳蹬上,,把右腳伸進三腳架另一邊的腳蹬上半圈半圈地踩。他扶住后架,,跟在后頭,。咣當我倒下了,又連忙扶起我,,沒事沒事,,繼續(xù)繼續(xù)。我就是跟保吾伯學會騎單車的,。
保吾伯十三四歲就進城學徒,,做過很多事,跑過很多地方,,是我們家親戚中最見多識廣的人。我最喜歡聽他聊天,。他說什么都有味,。我們搬過幾回家,每回都是保吾伯幫我們打點收拾,,手腳極是麻利,。我們家凡遇到什么事,第一個想起來要求助的,,必是保吾伯,。
如今,有什么事要再找保吾伯,,已經(jīng)找不著了,。當然,,太妃糖如今也看不到了。李四格呢,,興姑媽呢?他們也都不在了,。
我老家其實就在長沙縣,并不遠,,但我卻沒有再回去過,。因為老家已經(jīng)沒有親戚了。父親家雖然仍有親戚走動,,但都是從城里頭來的,。
沒有了親人的老家,現(xiàn)在是什么樣子呢?
本文刊于2017年2月8日《文匯報 筆會》,,原題“老家人”